小悦悦离开我们,已经三天了。因她的死引发的讨论和思考,仍在继续。
父母怎能那样大意?18路人何至如此冷漠?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拾荒阿婆的救人之举?世道人心真的沦落了吗?这个社会到底得了什么病?这名两岁女童的死,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,拷问着每个国人的灵魂。
或许,我们可以换个视角考虑问题,将“
小悦悦父母”“18路人”和“拾荒阿婆”都替换成“我们”,然后扪心自问:我,能否比他们做得更好?我们,能否为推动这个社会向真、向善、向美做些什么?
各领域知名专家十余人,现将他们最有价值的思考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呈现于此。
【焦点1】
父母为第一位责任主体
京华时报:对于这件事,也有人提出应该追究
小悦悦的父母疏于监护的责任。你怎么看?
邵建:
小悦悦的父母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宝贝女儿,我觉得现在再说他们的监护不力,这个对父母太不公平了,也没必要。这事如果放在欧美发达国家,追究家长的责任我一点意见都没有,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,特别是那些农民工身份的父母,他们的生存太艰难、太不容易了,每天劳作繁重,很难时时刻刻把孩子带在身边,总是有疏忽的时候。这种情况下再谈追究家长的监护问题,我感觉太奢侈了。
姚建龙:我是研究未成年人法的,从我的专业视角,我认为这首先是一起有关儿童保护的悲剧性事件,其次才是社会伦理道德问题。事件发生后,国内的媒体都在责备18名路人没有施救,而且把
小悦悦的父母看成是悲剧事件中广获同情的受害人。实际上,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讲,父母是儿童保护中第一位的责任主体,首先要把这个明确下来,才能讨论路人的冷漠问题。试问,孩子没有脱离父母监护,何来交通肇事?没有交通肇事,何来路人冷漠。父母和路人是第一和第三的顺序,现在没有讨论一,就直接跳到三了。
京华时报: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?
姚建龙:这与文化背景有
【焦点2】
法律逼不出道德也逼不出善
京华时报:
小悦悦事件发生后,出现了“立法惩罚
见死不救”的声音,你对此是否赞成?
陈光中:
见死不救是社会道德问题,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是要非常慎重的。法律的强制手段,不是一个万灵的膏药,这个社会不能什么事情都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来治理,这未免太依靠法律了。而且即便立法规定了,道德跟不上来,也会导致有人一看到别人受伤,为了不被追究责任,就跑掉了。这样不解决问题。
阮齐林:从法理上讲,
见死不救只是道德问题,不是法律问题。法律不能惩罚人不做出一定的行为,对
见死不救者不能追究任何的法律责任。如果进行立法追究,会使我们每个人的负担很重,也可能导致一些人看到这种情况就躲避,这样立法也是没有效果的。另外,对于路人从道德上谴责也要注意分寸。有些人是事后诸葛亮。对于当事者,他们当时不一定对现场情况了解得那么清楚。可能有的人既不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,自己又有很重要的事情,于是匆匆而过,这有可理解的成分。不要一味地指责路人冷血,在道德上做负面评价,付诸法律更加不妥。
邵建:
见死不救不是法律问题,而是一个道德问题,对于道德的问题千万不能立法。法律的存在,只是禁止你做什么,而不是强迫你做什么。
见死不救这一行为固然不善,但不是恶。这时法律如果出动,不仅是逼人为善,而且直接侵害一个人可以不为善的权利。法律作为人的行为的外在规范,逼不出道德也逼不出善。道德是心性问题,必须发乎其内。以为通过惩罚
见死不救之类的立法就可以引发见义勇为,就可以改善我们的道德,这是一种法律迷信。它会导致国人更加恐惧,以为做好事的成本更高了,更会想尽各种办法来逃避这类法律。结果使立法得不到落实,社会的道德状况也更加下坠。总之,道德问题的归道德、法律问题的归法律,道德的病不能靠法律医,立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
京华时报:如何进行立法设计?
朱永平:我主张把两种行为纳入法律去调整,但不是纳入刑法,而是纳入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。一种行为是见危不救或者叫怠于救助。怠于救助应定义为轻微的违法行为,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正是调整人们的轻微违法行为的一部法律。我们要设定,非职务的特定人群,对处于危险状况的人,要有通知、保护现场和实施一定救助的义务。如果不履行这三项义务,证据确凿,就可以进行一定处罚,最高拘留15天,还可以进行警告或罚款。第二种是对诬陷、讹诈救助者的行为,我认为也可以纳入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去调整。现在,诬陷、讹诈救助者的行为在我们社会已经造成了极坏影响,但却没有法律去调整。因此,我主张,既要惩罚见危不救或者怠于救助的人,又要惩罚诬陷、讹诈救助者的人。
京华时报:多数人反对对
见死不救进行立法惩罚,认为这是道德问题,不是法律问题,立法强制可能引发公众为逃避处罚而故意远离事故现场。
朱永平:任何法律制定之后,都会有人想去规避。我们不能片面理解法律和道德的关系,很多事情都是把道德的东西上升为法律的。另外,我们人人都可能处在需要被救助的状况,不能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,才知道路人冷漠的可怕,才知道立法的重要性,我们应该设身处地考虑这个问题。
京华时报:作为关系心理学家,你也是赞同对
见死不救进行立法的,你的理由是什么?
胡慎之:人类所有行为的动机只有两个,一个是趋利,一个是避害。对于助人的动机,本来我们是要趋利,比如会让我们心安。而当我们感觉不安全的时候,人类的动机就是避害为主,为了自保,我们就会选择不去助人。我们现在的环境,人与人之间是一个不安全不信任的关系,太多关于“救人者反被冤枉”的案例,让我们对做好事有担心,
小悦悦事件已经说明这一点。而如果立法规定
见死不救要受到处罚,人们就会重新思考趋利避害,假如我救助了,我还能得到良心的安定;假如我不救助,可能会受到处罚。因此,法律可以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,让人们对需要帮助者进行施救。
京华时报:可能也会有人为了避害,跑得远远的。
胡慎之:就算他跑掉了,他的心里还是会有很强烈的罪恶感,这会规范他的行为,下次再碰到这样的事情,他可能就不跑了。这是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的区别,法律会让人有罪恶感,而道德只会让人产生愧疚感。相比之下,罪恶感是很难消除的,而愧疚感会被一些合理化的东西消除。比如
小悦悦事件,有路人会想,自己没救,别人也没救,他的内心谴责就会小很多,这在心理学上叫做“旁观者效应”。
京华时报:有人提出,
见死不救毕竟不恶,如果立法会直接侵害一个人可以不为善的权利。
胡慎之:我们不要把它称之为善和恶的问题,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作为公民,我们都有责任去维护这个社会的生存环境。
【焦点3】
见义勇为是否需要立法促进?
应扩大见义勇为“义”字范围
京华时报:有人建议,为了让人们放心做好事,可以立法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。你怎么看?
朱永平:我非常赞同在全国立一部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法律。目前,全国各地绝大部分的省份和有立法权的市,对于见义勇为都作了地方性的法规或条例,但基本上都把见义勇为定义为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这样的概念,有的还提到要“不顾个人安危”,我认为这个概念把见义勇为里的“义”字框死了,应该把“不顾个人安危”删掉,把“义”的范围扩大化,把对路人的救助、把对危险状况的救助,把通知、保护现场和实施一定救助的义务都纳入到见义勇为的范畴里去,并在物质上对见义勇为者重奖。而且国外的立法理念也是在确认自己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才去救人。如果确认自己没有危险不去救人,才是怠于救助。
【焦点4】
如何改善社会道德环境?
重拾社会信任关键在重建政府信任
京华时报:人与人之间的信任,如何才能重拾?所谓“人情冷漠”的问题,如何才能解决?
陈光金:无可否认,我们当下信任水平有所下降。这一点,政府在司法、执法和行政领域是否按规则去办事很重要,到底是规则还是潜规则在起作用?这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关键。如果大家都按照规则来办事,就会有确定性,相互之间的信任就会提升。而规则大多数是政府制定的,要重拾社会信任,重建政府的信任是一个关键的问题,然后才谈得上社会的信任。
邵建:我认为有必要加强公民的道德意识教育,加强传统文化学习。在优良传统文化保留得好的社会,人们是乐于助人的,因为助人不需要付出很高的、意想不到的社会成本,他们享受自己因帮助别人而带来的内心的快乐。但在我们目前的社会,人们感受不到帮助别人的乐趣,还要提防自己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作为社会成员,都应该多学习传统文化,用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。另外,社会是一个网络,应加强社群建构,把彼此陌生的区域建设成熟人社会,加强人们互助性的联系,提高责任感。
京华时报:如何才能鼓励人们见义勇为?
迟夙生:我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呼吁。前几天,我和胡益华律师成立了“停止冷漠公益法律援助”律师联盟。如果以后有人主动救人遭遇讹诈,律师联盟将免费提供法律援助。我们的最大初衷就是消除好心人在助人为乐时的后顾之忧。通过这些引领,使耍赖者少耍赖,救助者少点麻烦。我认为目前用这些方式解决比较妥当。
谈方:我们的政府要通过这件事深刻反思,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发展。我所接触到的一些“好人没好报”的事情,大部分跟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有关,是他们没有担当起惩恶扬善的职责。很多好人在推诿扯皮中继续受到伤害。表面上受伤的是个人,实际上受伤的是整个社会道德。
最近我们说的文化体制改革,绝不能仅仅理解成是文化产业的发展,更需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进行加强,否则会形成误读。
要把精神文明建设,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放到最重要的位置。要明白文化体制的发展和改革是为了传承和承载这些东西的。而当务之急,我建议开展一次“好人有好报,恶人有恶报”的专项治理活动。就像打黑,打击黄赌毒一样的,在全国去调查摸底好人没好报的例子有多少。被冤枉的还他们公道,伤病的给予救治,因做好人去世的,要给予他的家人关爱。总之,温暖好人心。
关。中国人缺乏儿童权利的观念,认为孩子是父母的,父母失去了孩子很悲惨,要去同情,也就是以父母为重心考虑问题。父母当然是受害人,但是我们把重心向前移一步就会发现,儿童才是受害者。而谁造成了儿童受害现象,首先是父母没有监护好。
京华时报:有人提出,父母失去孩子已经很悲惨了,这时再去责怪他们太残酷。
姚建龙: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,这时还去责难小悦悦父母,甚至主张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,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。但撒盐是必要的消毒措施。这起事件中,小悦悦是一个只有两岁多的完全无行为能力人,她没有危险意识,她已离家百米,跑出去六七分钟后,她的母亲才到。中国的父母很多时候都没有对孩子暂时脱离监护会有危险的意识。他们总会有无数“理所当然”甚至“不得已”的理由,将未成年子女独自放任在危险的地方,认为他们没有办法,要忙着谋生。可是谋生的目的是什么?还不是让孩子生活得更好吗?我认为,孩子的监护与贫富没有关系,主要是父母对自己法律责任的认识。通过这起悲剧事件,我们应该让父母明白一个最简单、最浅显,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道理,那就是要看好自己的孩子。这是父母的法律责任,而且是沉重的法律责任。
编辑:张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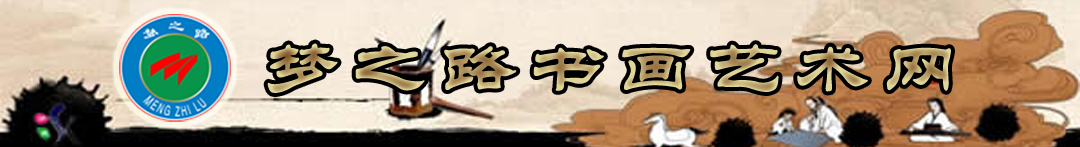
 最新评论
最新评论